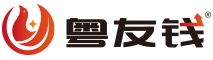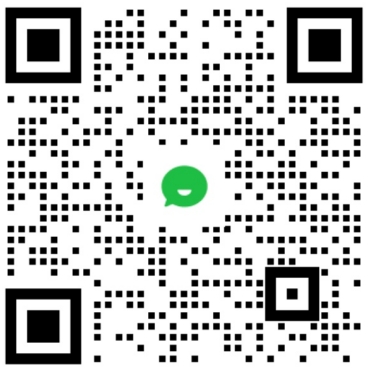近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3期)在线上举行。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陈彦斌主持,聚焦“大疫情持续冲击下的世界金融大动荡”,并邀请知名经济学家曹远征、张燕生、王晋斌、管涛、王涵联袂探讨。
1、全球金融动荡的关键原因是疫情冲击还是金融体系本身积累的风险?
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股市的系统性变化是受疫情冲击形成的大动荡。在疫情冲击下,这次大动荡暴露出一个金融的本质问题——高杠杆能否持续。在目前美联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通过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极度扩张稳定杠杆的办法能走多远?在油价低迷的状态下,美国页岩油等高负债行业能否可持续?在疫情冲击下,家庭收入来源被切断,负债压力较大,家庭负债表是否可持续?这三个问题表明高杠杆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这次金融动荡是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病”导致的。在这一背景下,疫情冲击暴露出了世界的种种矛盾,对世界和中国的金融市场以及大国在全球的位置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未来可能是一个去全球化、去中国化、去美国化、去全球产业链、去金融市场过去的地位的格局。同时,我们担心这次金融动荡可能会有二次爆发和三次爆发的风险。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认为这次全球动荡的关键原因是疫情冲击,但另一方面也受到过去十多年来长期的宽流动性和低利率积累的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疫情还没有结束,在目前大力度的救市政策下,只发生了股灾,还没有发生由股灾引发的市场恐慌进而演化成全面的流动性危机,也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是随着疫情的持续发展,对经济冲击压力加大,股灾是否会演变成金融危机值得高度关注。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王涵认为这一轮全球金融大动荡是金融体系本身的问题导致的。在过去的百年中,全球供需矛盾一直往供大于求的方向发展。供大于求的情况导致投资回报率偏低。2008年后,货币政策的宽松进一步摊薄了资金回报,因此,金融体系要想实现同样的收益,就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导致风险资产配置增加,如低评级债券,增加了金融体系的风险累积。这一轮的救助政策似乎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各大央行大规模释放流动性进一步摊薄了资本回报率,金融机构被逼进一步杠杆化,使得金融风险的进一步上升。
2、全球金融动荡到目前已基本结束,美股甚至出现了技术性牛市,将来金融体系二次探底风险有多大?
曹远征认为,虽然这一轮资产价格的动荡告一段落,但是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特别是,金融体系内部是否会爆发以去杠杆为代表的金融危机还需要密切观察。美联储以如此宽松的办法刺激经济导致了更大的风险,也对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如果高杠杆难以维持,那个时候爆发的金融危机会比2008年危机更严重。短期来看有两个风险需要大家高度关注:一是主权债务危机;二是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流动性危机。
张燕生认为,最坏的情况尚未爆发。当前,各国央行和财政部基本上把能用的政策工具都用上了,政策空间非常有限。具体来看,未来有以下风险:第一,中日韩是否会爆发二次疫情;第二,如果疫情向非洲、南亚、拉美国家蔓延,可能爆发人道主义危机;第三,如果疫情出现反复,由于疫情需要隔离,可能带来产业链、供应链的断裂危机。因此,对今后会不会出现二次反弹和二次金融动荡,我个人持非常审慎的观点。
管涛认为,虽然现在美股出现了大幅反弹,金融市场企稳,但不能说二次探底的风险已经完全消除。第一,美元指数仍处于高位,说明疫情冲击风险还没有完全消除;第二,纳斯达克指数的收复不代表疫情冲击恢复,因为科技股公司通过远程办公,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第三,美联储的放水主要流入了金融市场,导致股市的“虚高”,一旦经济复苏不及预期,矛盾可能会更加突出;第四,美国疫情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硬性复工将导致国内疫情反弹,同时复工复产的进程受制于其他地区的疫情防控,复工进度不一定能按预期实现;第五,美联储针对疫情过早过快的出手救助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王涵认为,短期内不能低估美股的反弹空间,但是同时也要警惕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在这一波美股的反弹主要得益于科技股,如果将标普500中的5只科技股剔除,则这一指数到现在为止仍是下跌的。从中期来看,科技行业的大规模扩张下,有明显的“毁灭性创造”的特征。即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供给端提高效率的同时,在需求端是毁灭需求的。当大量就业人群被AI替代时,最终需求会大幅下降。中长期来看,需求端的不足,会进一步加深供需矛盾,导致整体回报率的下降。
3、本次全球金融动荡中,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动荡似乎比震中心美国还严重,新兴经济体如何提高自己的抵抗力?对中国有什么启示?
曹远征认为,新兴经济体在疫情冲击下,风险在不断地暴露。首先,过去十年中,新兴经济体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在不断上升。其次,新兴经济体在资本外流的情况下,汇率大幅下跌,导致未来偿债压力的提高。对中国而言,要加快“本地化进程”以缓解货币金融原罪,期限错配、货币错配和结构错配的问题。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中国本身的需求,也是世界的需求,是解决本地区货币错配问题的体现。
张燕生认为,这次新兴市场爆发的强烈的金融动荡、金融危机、金融冲击是因为全球化已经进入到了下半场,即风险明显大于机遇。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可能结束,但是货币危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等高频率发生的问题现在开始一步一步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过去的全球化过程中,重视经济自由、政治自由,使全球效率发生了改善,但是全球化没有机制解决公平问题,这导致新兴市场无论是债务、货币、国际收支还是金融等方面的风险大大提升。对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而言,要联合抗疫,联合稳定产业链、畅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第一,东亚要联合扩大内需;第二,东亚要联合实现关键技术零部件的本地生产;第三,东亚要保持金融稳定。
管涛认为,疫情冲击新兴市场,发生了创记录的资本外流,主要原因是过去十年全世界宽流动性低利率的背景下,新兴市场的原罪更加严重,即新兴市场的货币是不可兑换的货币,所以必须要用硬通货对外支付,同时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需要到海外进行融资,这就导致了中长期的货币错配、期限错配等问题。对中国的启示:第一,经济稳、货币稳,经济强、货币强;第二,要在“雨天打伞,晴天补漏”;第三,要控制好货币错配和汇率敞口。
王涵认为,新兴经济体内部分化明显,这与本国疫情情况和经济情况相关。中长期来看,新兴经济体都面临着财政最后如何维持的问题。对中国而言,要保证汇率政策更加灵活,要为货币体系的重大变革做好准备,同时还要避免国内资产泡沫化的问题。
王晋斌认为,美元指数的走强,会使美元资产对全球吸引力的进一步上升,这有利于美元霸权的进一步巩固。在这样的状态下,对于新兴市场中的比较脆弱的经济体,当务之急还是疫情防控。对于整个东亚经济体而言,由于中日韩的疫情防控十分到位,目前比较重要的迅速推进中日韩自贸区。但是中国没必要参与“亚元”,人民币将来一定会成为区域性的强势货币。
4、疫情冲击下的全球金融动荡对中国影响路径与对策?
曹远征认为,疫情冲击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在现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有很大的内在缺陷,但是在疫情的进程中,全球出现了去人民币国际化的倾向。一是,各国央行进行货币互换,但是中国央行没有参与。二是,人民币没有进入数字货币。这对中国经济和人民币国际化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影响。
张燕生认为,疫情冲击对中国的影响,一是可能通过全球的货币金融动荡产生,二是可能由于油价和大宗商品的波动产生,三是可能通过全球经济衰退产生。对中国来讲最核心的问题是科技方面的去中国化,规则方面的去中国化,产业方面的去中国化,和货币方面的去中国化。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在规则、科技、产业、货币等方面不断做强;同时,还要主动与世界各国挂钩。
管涛认为,金融动荡对中国的影响路径是两个,一个是金融渠道,一个是实体经济渠道。金融渠道:一方面可能是信心危机的传染,另一方面,可能是本身市场避险情绪上升,导致集中抛售风险资产。实体经济渠道:世界可能陷入资产负债表的衰退,世界经济有长期持续低迷的可能性,这会导致中国的外需长期疲软。
王涵认为,要关注通胀层面上和地缘政治层面上的问题。中国的应对:第一,要加快改革,包括要素改革;第二,政策层面上,要聚焦民生、结构性问题;第三,加大开放;第四,避免大刺激,保留部分政策弹性空间,为极端情况做好准备。
王晋斌认为,中国在国际上取得今天的成就不依靠金融,而是靠制造业。人民币要想实现国际化,也要落在实体经济创新上面,要让中国市场能给投资者提供收益。所以,当下要想办法刺激需求,使科技的进步更上一个台阶,这是未来中国综合实力上一个台阶的核心要点。
广州明绮科技有限公司粤ICP备:19036361号
专业股票 期货操盘平台 ! 我们提醒您: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