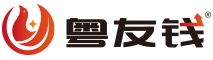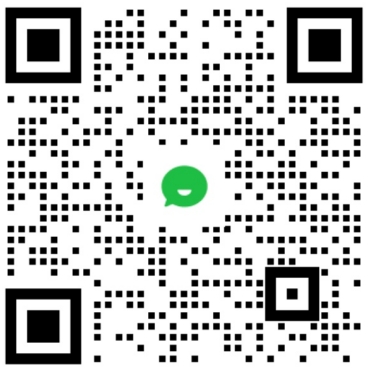近期,互联网贷款全方位收紧,从数据采集到贷后催收,从头到脚迎来集中整治与强力监管。在此背景下,早已引发各方关注但一直没公布统一监管文件的联合贷款,又重回舆论视野。毕竟头和脚管住了,没道理不给联合贷款一个明确说法。
但联合贷款,不仅仅是产品创新和模式创新,更带来了金融生态的深层次变革,利弊优劣,三句五句说不清楚;如何监管,也远非“禁”与“不禁”所能涵盖。
联合贷款因何而生?
联合贷款并不神秘,很多人以为它是金融科技公司的模式创新,其实不过是银团贷款的模式化应用。
监管将银团贷款界定为“由两家或两家以上银行基于相同贷款条件,依据同一贷款合同,按约定时间和比例,通过代理行向借款人提供的本外币贷款或授信业务。”联合贷款也是这样,两家或两家以上持牌放贷机构,基于协议安排联合发放贷款。
银团贷款里,有牵头行、参与行和代理行之别,在“信息共享、独立审批、自主决策、风险自担”四原则下,各方权责分工各异。牵头行负责贷前调查、确定贷款条件并组建银团,代理行代表大家进行贷款发放、收回和统一管理,其他参与者统称为参与行。
联合贷款里,基本也是一家机构负责获客、贷前初审、贷款管理和回收,其他持牌机构在独立审批、独立决策并与借款人独立签署合同的基础上参与进来,同样要遵循“信息共享、独立审批、自主决策、风险自担”等基本原则。
银团贷款又称辛迪加贷款,为大额借款项目而生,合多家银行之力,满足大型基建和集团公司贷款需求。联合贷款,则为小额普惠金融而生,合多家机构之力,优势互补,降低成本,为普惠金融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也助力金融机构科技转型走上快车道。
(1)破局普惠金融难题
小微群体贷款本金小,利润薄,金融机构做小微贷款,往往无利可图,要么弃之不做,要么提高定价。前者导致融资难,后者产生融资贵,顾此失彼,普与惠不能兼顾。
破局之策,便是降低综合成本(如资金成本、获客成本、风控成本、运营成本等),综合成本低一些,普惠金融的空间就多一些。
单一金融机构,固然可通过模式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降低成本,但幅度有限。相比之下,联合贷款取各家金融机构所长,让擅长获客的去获客、擅长风控的做风控、吸储能力强的多提供资金、强于运营的做贷款管理,可把综合成本压降至理论上的最低值,普惠金融空间自然就出来了。
2016年末,央行征信系统中仅4.27亿人有贷款记录;2019年6月增至5.48亿人。表明这两年半时间内有1.2亿人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支持,由无贷户变成有贷户。这是普惠金融的成绩,又何尝不是联合贷款和助贷的功劳。
(2)助力金融机构科技转型
科技已成为金融机构第一驱动力,但科技转型不能嫁接在空中,需在业务转型中落地。
全国性银行基础厚、实力强,自力更生还算条出路;区域性银行底子弱、基础差,除了银行牌照带来的资金优势,在获客、风控、运营等方面均有困难,完全靠自己,业务动不起来,科技转型更是空中楼阁。
联合贷款聚合各方力量,为优势资源互联互通提供桥梁。借助联合贷款,全国性银行可以不必自己造轮子,科技转型步入快车道;区域性银行更是可以在开放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
在这里多说一句。虽然相比单打独斗,联合贷款和开放平台为金融机构转型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但金融机构是否愿意转型、能否转型成功,还是取决于自己。当前市场中有很多声音,认为联合贷款和助贷加剧了持牌资金方的管道化和空心化,这就好像那些互联网让孩子沉迷于网游的指责一样,并不能令人信服。
生态重构与场景崛起
联合贷款连通了银行资金和互联网流量,释放出巨大能量,消费金融因此得以快速增长。增长强化增长,消费金融风口效应形成后,引来各方加速布局。如据奥维咨询估算,2018年末,线上消费贷款余额1.5万亿元,较2016年实现近四倍增长。
行业高速发展中,一些机构趁机成为新模式里的重要节点。这些节点连通四方资源,开放平台和开放银行模式便应运而生。演化至此,金融业的生态模式已然有了深刻的变化——金融与场景深度融合。
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场景方凭借庞大的用户流量,有实力有资格与金融机构洽谈助贷和联合贷款合作,而助贷和联合贷款的发展,进一步加速金融与场景的融合,巩固了用户在场景中获取金融服务的习惯。
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场景方深度融入金融生态圈,带来了各方权责利关系的重构。重构中有冲突,更有和解。
从顺序上看,金融机构率先反应,从排斥到竞争再到合作,用了大概三年时间(2013-2016年),最终以开放平台和开放银行崛起为标志,宣告双方全面和解,共同完成了金融业务模式的重塑。但厘清金融机构与场景方的关系只是第一步,如何厘清场景方与用户、场景方与监管的关系,则成了新挑战。